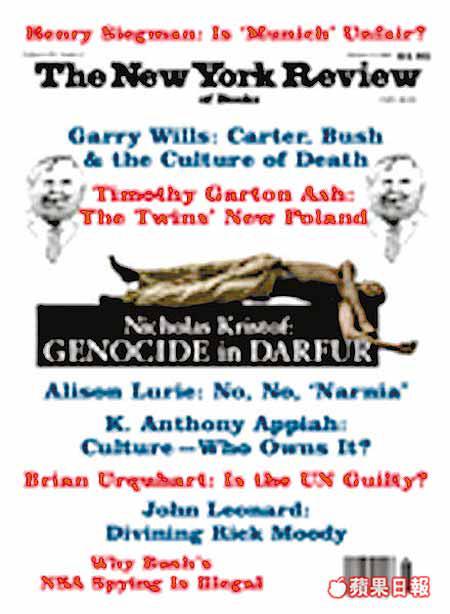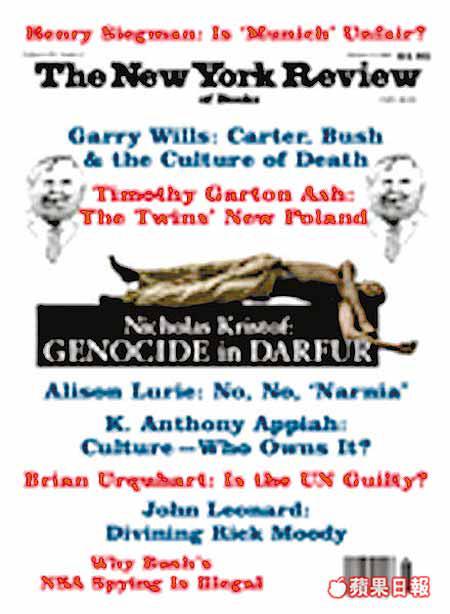
梁文道 文化評論員
每次收到《紐約書評》(TheNewYorkReviewOfBooks)和《倫敦書評》(LondonReviewOfBooks),我首先翻閱它們的最後兩頁,因為我愛看那些分類廣告裏徵友求愛的小方塊。05年12月1日的《倫敦書評》在第39頁上登了這麼一則啟事:「我們很高興地在此宣佈:終於有一樁由這個版面締結的婚姻宣告破裂了。一度是沙漠的地方,現在成了徹底的荒原。別說我們沒有警告過你」。這到底是甚麼地方?這到底是怎麼樣的版面?
《紐約書評》和《倫敦書評》是大西洋兩岸英語世界中最頂尖的書評雜誌,能夠被它們評介的新書,不一定是最暢銷的書;經過它們稱讚,也不一定會變得更好賣;但凡是它們討論過的,必定是知識界裏最值得注意,甚至是最重要的書。所以按期瀏覽這兩份雜誌,就等於掌握了英語知識界的最新動向。我喜歡它們多過資格更老內容更廣泛的《時報文學增刊》(TheTimesLiterarySupplement簡稱TLS),因為它們的文章夠長,內容深入,作者發揮的空間大,讀者讀得更痛快。而且TLS沒有徵友廣告。
雖說是書評,但這兩份刊物的文章其實更像是專論,常常把幾本相同主題的書放在一起評比,以抓住學界脈搏,看看大家最近都在關心甚麼話題。書評之外,還有藝評與詩,更重要的是專題評論。《紐約書評》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就是美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發表議論的重鎮,也有人說它是紐約派文化人的旗艦,像蘇珊.桑塔格和以賽亞.柏林這樣的知名人物有不少是它的長期作者,他們許多傳誦一時的名篇都是當年《紐約書評》首發的重頭專論。
最該令中國學者看了之後汗顏的,是這兩種雜誌的作者雖不乏成名學者,如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Spence)和法學家杜沃金(RonaldDworkin),但他們可以拋開學院文體的包袱,採用一種看得懂易親近的筆法,把學術界中的重大辯論深入淺出地介紹給閱讀大眾。反觀中國學界,特別是自然科學的,很少有這種習慣跟意願,去為一般讀者和學術殿堂搭橋。就算少數學者肯寫科普文章,也苦在中文世界沒有參照,不知道分寸該怎麼掌握。反觀英美,《紐約書評》傳統早成,典範俱在,大學教授一旦決定動筆寫些東西給象牙塔外,拿《紐約書評》的風格當範本準沒錯。
《紐約書評》和《倫敦書評》的對象不侷限在學院以內,但這並不表示任何人都可以隨手拿起來,毫無困難地從頭看完,因為它們對讀者的知識水平還是有一定要求的。看這兩份雜誌的,應該就是所謂的閱讀大眾。他的職業可以是律師,也可以是小書店店員;可以是退休公務員,也可以是中學生;總之他得是個熟練的讀者,興趣廣泛,無論是文學、經濟、政治、歷史還是物理,只要是最新的發現都能挑起他的好奇心。
而我就是對這樣的讀者感到好奇。這兩份雜誌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們把讀者組織成了一個跨地域跨年歲的「文化共和國」。不管你住在地球的哪個角落,只要你是它們的讀者,它們刊登的評論就反映了這個抽象團體的共同關懷。身為這兩份雜誌的訂戶,我很想知道那些和我同住在一個抽象國度裏的國民,到底在現實世界裏是怎麼樣的人,長甚麼樣,吃甚麼菜。所以我看它們的徵友廣告。
《紐約書評》果然是美式風格,直接、明快、單刀直入,比如以下這則廣告:「真人比照片還漂亮(至少人們這麼說),聰明、纖瘦、性感,還帶着點無厘頭的幽默感……頭腦活潑、笑容動人、熱愛旅遊、對於新觀念懷抱着無比熱情。成功而高調的紐約居民。帶有北歐血統。煮食技巧不錯。喜歡慢跑、單車、巴塞羅那、黑比諾紅酒、新MoMA(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正在尋找一個身體良好,吸引人的專業男士」。原來《紐約書評》的讀者都是這樣的人?聽起來很「正」呀!但這些廣告看得多,你自然會厭倦,哪一份雜誌的徵友廣告不是自吹自擂?
所以,為了突出自己,有人選擇強調自己的行業,例如「紐約某大學的文學教授,熱愛友誼、鉅著、教學、政治以及人性、自然和藝術中的一切美好事物。想找一個年輕點的女性與我分享」,那這位教授多少歲呢?他也坦白地寫了出來,71歲。看徵友啟事,很能印證我們的偏見,上年紀的人也需要伴侶,只不過他們的機會越來越少,所以要在雜誌上登廣告,即使成功人士也不例外:「曾經是普利茲獎得主的出版社高級主管,現在是個藝術家。正在尋找一個受過良好教育而又活躍熱情的男人,62歲以上」。
這類廣告難免誇張,有時深怕簡單的形容詞不足以表達自己的秀異,還要用上一些公眾臉孔來豐富讀者的想像。看看這個:「不經意的美麗,優雅華麗但又實在的曼哈頓女人。纖細腿長如戴安姬頓,古典得像嘉芙蓮丹露。從前當過模特兒,而且經歷過有趣的文學生涯。很想找人和我分享巴黎與不丹、艾慕杜華的電影、跟普羅旺斯魚湯。」如果你覺得這有點假過頭了,可以考慮這個簡單實在的男人:「嗓音性感,身體壯健,想找一個人一起探索無邊的性幻想」。
《紐約書評》的立場一向是左傾自由派,創刊初年就以投入反越戰運動著稱,在新保守主義當道的過去二十年有點沉寂,九一一後又重新活躍起來,成為反布殊知識份子發炮的基地之一。所以它的讀者應該也有相近的政治傾向,果然,一個「住在紐約上西城的活躍學者」除了自我介紹「聰明、有藝術天份,樂觀感性」的這一面,還特別強調自己「致力於所有人的平等權利、社會正義和社會變革」。假如這是《紐約書評》讀者們的集體傾向,就很難怪有個自稱「喜歡莫札特的鋼琴奏鳴曲與哈金小說」的傢伙要連續登好幾期的廣告了,因他還標榜自己是《經濟學人》讀者。我們不是不看《經濟學人》,只是不能把它當成賣點,懂嗎?你這個新自由主義的走狗!
至於《倫敦書評》,要比《紐約書評》年輕得多,其全球訂戶更不超過三萬,但越辦越有活力,頗有後來居上之勢。除了老牌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Hobsbawn)近年紅遍歐美的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杰克(SlavojZizek)也是它的作者,筆陣一時無兩。前兩年它甚至冒險地在人文薈萃滿街書肆的倫敦開了一家自己的書店,宣稱絕不售賣低格調的暢銷書,還定期舉辦講座與研討會,要把圍繞着它的抽象社群落實成活生生的人際網絡。有人說這家「倫敦書評書店」在短短兩三年裏,已經辦成了全倫敦最好的書店。
光從徵友這回事來說,《倫敦書評》就比《紐約書評》用心得多。它有個大洋彼岸的前輩鬥不過的好處,就是它的書店可以拿來舉辦不定期的「單身之夜」。去年12月9日它才搞過一次,入場費要8英鎊,但買書有九折,還可享用葡萄酒跟點心,現場音樂是一個叫做YammeiWu的中國人彈奏Zheng(箏)。有些朋友常夢想在書店裏發生艷遇,最好是專心找書時不小心撞到身旁的妙齡女子,雙方的書都鬆手掉到了地上,雙方又一起蹲下來撿書,還要不小心摸到對方的手,再靦覥地相視一笑,輕輕說聲對不起……我在他們的書裏見過類似的情節,但電影和MTV把它們實現得更徹底,看起來十分土氣而且猥褻。來參加「倫敦書評書店」單身之夜吧,丟下你那老土猥褻且偷偷摸摸小家子氣的幻想,光明正大地在書架間調情,還可保證被你撞到的那個人掉在地上的書,一定不是《教你做個有錢人》。
《紐約書評》的徵友小方塊常常出現「幽默感」這三個字,但《倫敦書評》讀者的幽默感是乾脆表現出來的。且看這一則:「我是40歲的《倫敦書評》女性訂戶。和我在一起,可以省下你的訂閱費」。還有「你想為我的書架帶來驚喜嗎?尋找一個三十出頭的女子。來建議我應該添加甚麼書進去,最好還可以幫我丟掉一些」。「有五件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東西:我花園裏薰衣草的香味,總叫人渴望的夏天,大衞連的電影,《倫敦書評》以及每天下午4點半到午夜的獨處時刻──如果你在這段時間和我說話,我一定會殺了你!有意者請來信」。
十多年前,我曾經在一份文化雜誌寫專欄,偶而兼職打雜。那份雜誌也有整版的分類小廣告,時常在死線之前還沒填滿(可見香港文化雜誌的處境),於是我就得坐下來臨場發揮,虛構幾則廣告出來,充實版面。因為這段經歷,我看《倫敦書評》的時候就很自然地起疑,不知這些廣告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世界上不大可能有這樣的事:「三十多歲的女性,朋友們都說我性感美麗。我愛歐陸哲學,迷上布拉格,ColePorter是我的偶像。我有一段穩定的婚姻,丈夫很有錢而且全力支持我。現在我想要一個part-time男伴,分享我的靈魂跟肉體。未婚者免問。」世界上會有這樣的事嗎?
更離譜的還有「最初我帶着良好意願在這裏登廣告,如今我發現自己名列證人保護計劃。《倫敦書評》,真係多得你唔少!女性,42歲,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二就會有新的身份和新的地址。我要找一個45歲以下的男人,他不能有可追索的電話號碼,車尾箱得有一大堆的備用汽油。拒絕抽煙人士,拒絕黑幫成員(我受夠了)」。最後再抄一則:「你知道百分之八十二的《倫敦書評》男性讀者都是忍者嗎?我不是其中一員,但我的功夫是比較老派的,所以只能讓少數人知道我的秘密,我可是個能在耳語間發出『氣』的人。現在我住在父母多出來的房子,躲避我前妻那幫律師,但我一定會報仇。認識我,我教你功夫」。
《倫敦書評》的徵友廣告如此可觀,是有原因的。它這兩版的固定贊助商是Taittinger香檳,每一期最出色的啟事人可以收到一瓶香檳當獎品。所以這兩版廣告成了讀者們的徵文比賽,登廣告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找一個真正的伴侶,倒不如說是為了showoff和一瓶酒。
至於我自己,看了這麼多年的廣告,有沒有寄過信給那些老教授和女畫家?又有沒有自己也發一則廣告的衝動呢?且引一則《倫敦書評》最短的廣告:「虛無主義者甚麼都不尋求」(Nihilistseeksno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