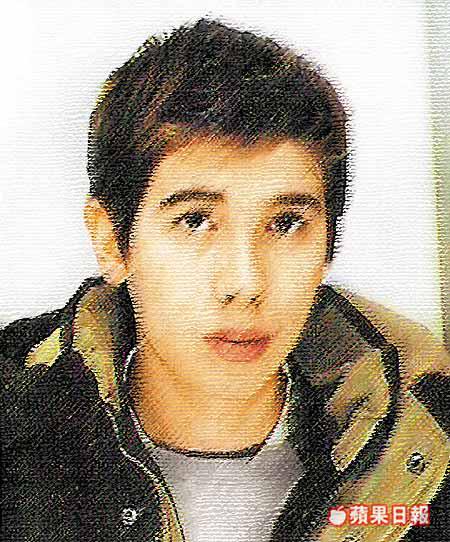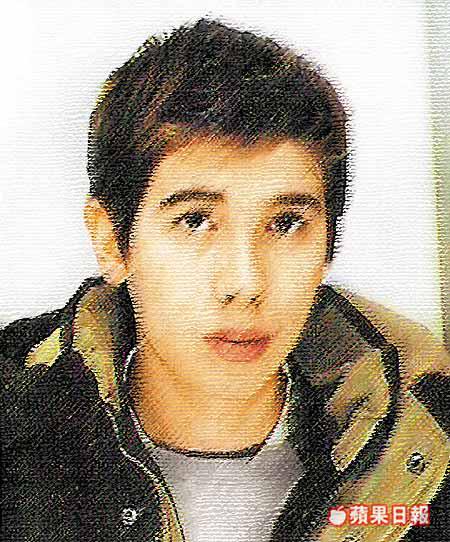
菲力普給安德烈的信
誰說香港沒文化?
安德烈,
住了兩年香港以後回到德國,還真不習慣。香港是超級大城市,皇冠堡是美麗小鎮,這當然差別夠大,可是我覺得最大的差別還是人的態度,文化差異,實在太大了。
你說香港沒有咖啡館,沒有安靜逗留的地方,香港沒有文化。我覺得,安德烈你還不懂香港。香港確實很少咖啡館,尤其是那種很安靜的,可以讓人泡一整個下午的很有情調的咖啡館。可是,這樣就代表「香港沒有文化」嗎?
回到德國以後,我週末的日子大概都是這樣過的:放了學先回家吃中飯,然後和兩三個同學約了在小鎮的咖啡館碰頭。在一個靜靜的咖啡館裡頭,你就會看見我們一堆十六歲的人聊天,聊生活。喝了幾杯Caf?Macchiatos以後,天大概也黑了,我們就轉移陣地到一個小酒吧去喝幾杯啤酒。德國的小鎮酒吧,你知道嘛,也是安安靜靜的,有家的溫馨感。
我在香港的週末,放了學是絕對不會直接回家的,我們一黨大概十個人會先去一個鬧烘烘的點心店,吃燒賣蝦餃腸粉。粥粉麵線的小店是吵死了沒錯,所有的人都用吼的講話,可是你很愉快,而且,和你身邊的人,還是可以高高興興聊天。
吃了點心和幾盤炒麵以後,我們就成群結隊地去市中心,逛街,看看櫥窗,更晚一點,就找一家酒吧闖進去。
對,就是「闖進去」。在德國,十六歲喝啤酒是合法的,香港的規定卻是十八歲。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德國少年在香港進酒吧雖然不「合法」但是很「合理」。你說守在酒吧門口的人會不會擋我們?告訴你,我們假裝不看他,就這樣大搖大擺走進去,很少被擋過。我想,我們這些歐洲青少年在香港人眼裡,可能十六歲的都看起來像二十歲。常常有人問我讀哪間大學。MM在城市大學教書時我就說城大,MM到了港大我就說港大。
我們點可樂,有些人會喝啤酒。我偶爾喝杯啤酒(你不必多嘴跟MM說喔!)
(你去過深水灣嗎?那裡常有人烤肉,整個下午,整個晚上,香港人在那裡烤肉,談笑,笑得很開心。)
MM說,她買了一堆書以後,到處找咖啡館,很難找到,跟台北或者歐洲城市差很多。我想反問:那在德國怎麼樣呢?你試試看下午四點去找餐廳吃飯。吃得到嗎?大多數德國餐廳在下午兩點到六點之間是不開火的──他們要休息!
或者,在德國你三更半夜跟朋友出去找宵夜看看,包你自認倒楣,街上像死了一樣。
所以,你只要比一比我的德國週末和我的香港週末,兩邊的文化差異就很清楚了。老實說,我一點也不覺得香港沒有文化。
總體來說,我喜歡香港勝於德國。香港是一個二十四小時有生命的城市,永遠有事在發生。而且,在香港真的比較容易交朋友,香港人比德國人開朗。我在香港只住了兩年,在德國十四年,但是我在香港的朋友遠遠多於德國。昨天剛好跟一個義大利人談天,她在德國住了好幾年了。她說,德國太靜了,靜得讓人受不了。德國人又那麼的自以為是的封閉,芝麻小事都看成天大的事。
我跟她的感覺完全一樣,而且覺得,中國人跟義大利人實在很像:他們比德國人吵鬧喧嘩,是因為他們比德國人開朗開放。
香港唯一讓我不喜歡的,是它的社會非常分化。譬如說,我的朋友圈裡,全部都是國際學校的人,也就是說,全是有錢人家的小孩,付得起嚇人的昂貴學費。半年來你的交往圈子只限於港大的歐洲學生,幾乎沒有本地人,你說原因很可能是語言和文化差異造成隔閡,可是我自己的經驗和觀察是:有錢沒錢,才是真正的劃分線。譬如說,我在香港整整住了兩年,幾乎沒有認識一個住在公屋裡的人。而我們家,離「華富」公屋不過五分鐘。比較起來,德國的階級差異就不那麼的明顯,不同階級的人會混在一起。我的朋友裡頭,家境富有的和真正貧窮的,都有。
我覺得你在香港再住久一點,那麼香港的好處和缺點你可能就看得更清楚了。
菲力普
安德烈給媽媽的信
二十五萬人算多?
MM,
有時候我在想:香港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對香港是有些批評的,可是我還是喜歡這個城市,而且蠻關心它的發展──我決定去參加十二月四號的遊行。
我們離開遊行大街的時候,你問那個計程司機──他看起來像三十多歲的人吧?你問他為什麼沒去遊行,我當時在想,MM真笨,怎麼問這麼笨的問題!他沒去遊行,當然是因為他得開車掙錢,這有什麼好問的。
結果他的回答讓我大吃一驚。他說,「幹嘛遊行?民主不民主跟我有什麼關係?這些人吃飽沒事幹!」
二十五萬人遊行(警方說六萬人),主辦單位好像很興奮,你也說,不錯!可是,MM,這怎麼叫「不錯」呢?你記得二零零三年反伊拉克戰爭的遊行嗎?羅馬有三百萬人遊行,巴塞隆納有一百三十萬人,倫敦有一百萬人上街。而這些城市的人口是多少?
羅馬──六百萬。
巴塞隆納──四百六十萬。
倫敦──七百四十萬。
當然,湧進市區遊行的人來自城市周邊一大圈,不是只有羅馬或倫敦城市裡頭的人,但是你想想,羅馬人、巴塞隆納人、倫敦人為什麼上街?他們是為了一個距離自己幾千公里而且可能從來沒去過的一個遙遠得不得了的國家去遊行,還不是為了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問題、自己的直接未來。相對之下,香港人是為什麼上街?難道不是為了自己最切身的問題、為了自己的自由、為了自己的孩子的未來?為了自己,卻也只有二十五萬人站出來──你能說這是「不錯」嗎?
我也許無知,或者有歐洲觀點的偏見,但是我真的沒法理解怎麼還有人質疑遊行的必要。
遊行前幾天,我還在報上讀到大商人胡應湘的一篇訪問,他把正在籌備中的遊行稱為「暴民政治」,還拿天安門的流血事件來做比較,說遊行抗議對民主的爭取是沒有用的。他的話在我腦子裡驅之不去。這個姓胡的好像完全不知道東德在一九八九年的百萬人大遊行──柏林圍牆倒塌了。他好像也完全沒聽說過甘地爭取獨立的大遊行──印度獨立了。他好像也完全不知道一九六三年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掀起的大遊行,促進了黑人人權的大幅提昇。難道這個大商人對柏林圍牆、對甘地、對馬丁.路德.金一無所知?
政府一意孤行時,通常遊行抗議是人民唯一可以做的迫不得已的表達方式。我不是說每個人都應該上街遊行,可是我認為每個人至少應該把問題認識清楚,明確知道那些主張上街的人的訴求是什麼,再決定自己的立場。
回到那個計程司機。他在聽廣播,所以你問他,「遊行人數統計是多少?」那時候還是下午五點左右。他說,「大概十萬左右。」你說,「不壞。」他就帶著一種勝利的微笑,說,「哈,可是很多只是小孩!」
確實的,遊行的隊伍裡小孩特別多,很多人推著嬰兒車來的。也有特別多的老人家。很明顯,那司機的意思是說,十萬人不算什麼,因為裡頭很多是小孩,而小孩不算數。
我的新聞寫作課的指定作業是訪問遊行的人,幾乎每一個被我問到「為何遊行」的人都說,「為我的下一代」。
我真的很感動,MM。他們要求的僅只是一個民主時間表,他們沒有把握自己是否見得到民主,但是他們站出來,是為了要確保自己的孩子們一定要見得到香港民主那一天──他們可以忍受自己沒有民主,但是他們在乎下一代的未來。我想很多人當年是為了逃避共產制度而來到這個島,現在好像老的陰影又追上來了。
遊行的人群裡那麼多孩子,他們「不算數」嗎?我卻覺得,不正是孩子,最值得人們奮鬥嗎?
出門前,我問了幾個歐美交換學生去不去參加遊行,發現他們都不去,說要準備期末考。我有點驚訝,咦,怎麼面對歷史的時刻,那麼不在乎?四零年代西班牙戰爭的時候,歐美大學生還搶著上戰場去幫西班牙人打自由之仗呢。不過,我是不是也該為我的同學辯護呢?如果不是新聞寫作的作業,搞不好我自己也不會去。畢竟,一個地方,如果你只是過客,你是不會那麼關心和認真的。
但是讓我真正驚奇的,還是到了遊行現場之後,發現中年人、老年人、孩子佔大多數,年輕人卻特別少。感覺上大學生的比例少得可憐。大學生哪裡去了呢?通常,在第一時間裡站出來批判現實、反抗權威的是大學生,很多驚天動地的社會改革都來自大學生的憤怒,不管是十九世紀的德國還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歐美。你告訴我還有中國的「五四」運動。所以我以為維多利亞公園當天會滿坑滿谷的大學生,結果相反。
於是我回想,是啊,在港大校園裡我也沒看見學生對遊行的訴求有甚麼關心。幾張海報是有的,但是校園裡並沒有任何關心社會發展的「氣氛」,更別說「風潮」了。
期末考比什麼都重要。
好吧,MM,你說這次遊行留給我什麼印象?一,一「小」撮人上街去爭取本來就應該屬於他們的權利;二,一大堆人根本不在乎他們生活在什麼制度下(只要有錢就行);三,大學生對政治──眾人之事──毫無關切;四,大學只管知識的灌輸但是不管人格的培養和思想的建立。
這就是我看到的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的香港。
這樣的香港,將來會怎麼樣呢?
安德烈
龍應台給兒子的信
為孩子走路
親愛的安德烈,菲力普,
十二月四日香港大遊行的前一天正巧是台灣的縣市選舉;選舉結果,執政的民進黨以一種你可以說是「被羞辱」的方式失去大部分地區的支持。第二天的香港遊行裡,你記不記得其中一個旗幟寫著:「台灣同胞,我羨慕你們可以投票!」
和菲力普參加過兩次七一的遊行,一次六四的靜坐紀念。(這也是你懷念香港的部分嗎,菲力普?如果是,下回法蘭克福如果有反伊拉克戰爭的遊行,你會去嗎?)香港人還沒學會台灣人那種鼓動風潮、激發意志的政治運動技術;如果這四公里的遊行是台灣人來操作的話,會很不一樣,台灣人會利用各種聲音和視覺的設計來營造或者誇大「氣氛」。譬如很可能會有鼓隊,因為鼓聲最能激勵人心,凝聚力量。香港人基本上只是安安靜靜地走路。
和你一樣,最感動我的,是那麼多孩子,很多人推著嬰兒車,很多人讓嘻笑的兒童騎在自己的肩上。問他們,每一個人都說,「我在為下一代遊行。」「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情懷,充分體現在香港人身上。
他們遊行的訴求,低得令人難過:香港人不是在要求民主,他們只是在要求政府提出一個時間表,只是一個時間表而已。他們甚至不是在要求「在某年某月之前要讓我們普選」,他們只是要求,「給我一個時間表」!
在我這外人看來,這是一個「低聲下氣」到不行的要求,在香港,還有許多人認為這個訴求太「過份」。
香港人面對事情一貫的反應是理性溫和的,他們很以自己的理性溫和為榮──嘲笑台灣人的容易激動煽情。我也一向認為,具有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一旦實施民主,絕對可以創造出比台灣更有品質的民主(台灣的民主沒有「品質」可言),因為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是民主兩塊重大基石。但是十二月四日的遊行,給了我新的懷疑:
溫合理性是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的外在體現,在民主的實踐裡是重要的人民「品性」。台灣人比起香港人不是那麼「溫合理性」的,因為他們是經過長期的「抗暴」走出來的──抗日本殖民的「暴」,抗國民黨高壓統治的「暴」,現在又抗民進黨無能腐敗、濫用權力的「暴」。在台灣,愈來愈多「溫合理性」的人民,但是他們的「溫合理性」是在從不間斷的「抗暴」過程裡一點一滴醞釀出來的。台灣人的「溫合理性」是受過傷害後的平靜。
香港人的「溫合理性」來自哪裡?不是來自「抗暴」;他們既不曾抗過英國殖民的「暴」,也不曾抗過共產黨的「暴」。在歷史的命運裡,香港人只有「逃走」和「移民」的經驗,沒有「抗暴」的經驗。他們的「溫合理性」,是混雜著英國人喝下午茶的「教養」訓練和面對坎坷又暴虐的中國所培養出來的一種「無可奈何」。
所以香港人的「溫合理性」在程度上,尤其在本質上,MM覺得,和台灣人的「溫合理性」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台灣人常常出現的粗野,其來有自,香港人從不脫線的教養,其來有自。
這樣推演下來,我親愛的孩子們,讓我們來想想這個問題:
香港人的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在民主實踐中,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在沒有民主而你要爭取民主的時候,尤其是面對一個巨大的、難以撼動的權力結構,這種英國下午茶式的「教養」和中國苦難式的「無可奈何」,有多大用處?
我第一次想到這個問題,安德烈,菲力普,你們說呢?
至於大學,安德烈,你說在香港,「大學只管知識的灌輸但是不管人格的培養和思想的建立」,老實說,我嚇一跳。大學成為一個技術人員的訓練所,只求成績而與人文關懷、社會責任切割的現象,不是香港才有。中國、台灣、新加坡,都是的。你說的還真準確。但是告訴我,孩子們,難道你們在歐洲所接受的教育,不一樣嗎?你們能具體地說嗎?
不能再寫了,因為要去剪頭髮。菲力普,啤酒即使淡薄,也不要多喝──你還有什麼沒告訴我的秘密?
MM
2005-12-08於台北
小注:
太多人問了,所以:
菲力普:16歲
安德烈:20歲
MM:53歲
1.他們都是真人,不是虛擬的。而且是母子關係。
2.所有的通信都是真實的,不是小說。
3.菲力普寫德文,安德烈寫英文,MM負責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