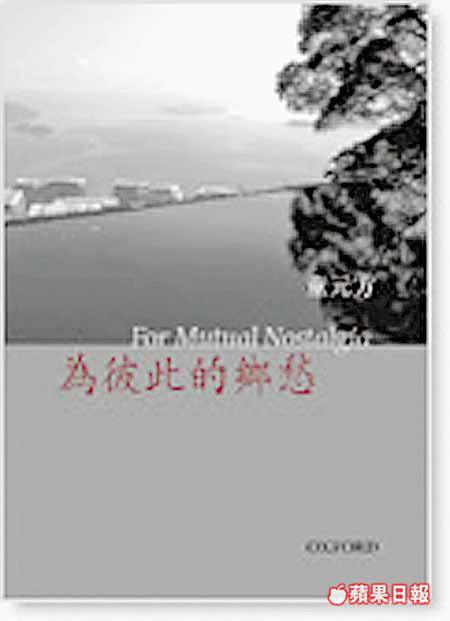童元方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副教授
這是我最近兩三年寫的散文所結的集子。大部分是在香港寫的,也偶有在台、或在美寫的。要起一個與內容多少相關的書名,總是朦朧地想起一個英文字「Nostalgia」。相應的中文呢?是鄉愁,還是憶昔?或是鄉愁與憶昔兼而有之?卻因此想起兩三個小故事來。
先由一個與我最沒有關係的故事說起:
「ForMutualNostalgia」是愛因斯坦在一本書上的題簽。這本書是有關布拉格這座城的攝影集,是愛氏去世前兩年的一九五三,送給他最後一位女朋友約翰娜的生日禮物。這不是相當於中文的「為彼此的鄉愁」嗎?為甚麼不譯為「共同的」呢?雖然是大家共有的,但贈書之事只涉及彼此二人。至於故事的原委也可長話短說。
愛因斯坦在一九一一年,一家四口忽然去了布拉格,但只待了十六個月,就又回瑞士了。在剛到布拉格時是很興奮的。他與老友們寫信說,那裏的風景優美,而居處也有電燈。但並無多久即發現水要煮沸才可以喝,卧床竟然有捉不完的跳蚤;大學裏有許多表填不完,有層層學官要應付。學生的程度也談不上,更沒有可以切磋的朋友。那十六個月,愛因斯坦對布拉格總括的形容是:「半野蠻的地方」,當然越快離開越好。但這些畢竟還是浮面的理由,及至最近我知道了愛氏晚年那位女伴也是從布拉格來的,愛氏在贈書上寫出「Nostalgia」這個字。我好奇起來:懷甚麼鄉呢?又憶甚麼舊呢?
我只喜歡看愛氏傳記中的零碎細事,何況這個布拉格的十六個月實在是愛因斯坦一生的分水嶺,也是他感情世界中起伏的關鍵。這些古人往事,何須擔憂,而仔細推求起來,竟也驚心動魄。
布拉格固然是約翰娜的故鄉,但愛因斯坦在布拉格時她才十歲,愛氏自己是三十二歲罷。到了一九二九年,約翰娜曾於柏林為愛氏整理過凌亂的書架,編過一本藏書目錄,作為愛氏五十歲的生日禮物。那時候約翰娜早就是奧圖.凡塔的妻子,而凡塔本人,愛氏倒是在布拉格就認識的。愛氏在布拉格時煩中稍樂的時光,多是在凡塔老家的沙龍。與凡塔在柏林的重逢,喚起過二十年前的記憶;但與約翰娜在柏林的來往,可以說為時甚暫。那麼,所謂「MutualNostalgia」又如何說起呢?
「Nostalgia」這個字之於愛氏,寫在贈給約翰娜的布拉格的攝影集上,是捕捉城市的光影呢?還是憶起了凡塔家的大宅?使後來離群索居於普林斯頓小鎮上的兩人,有這可憐的「共同」之地。實在是愛因斯坦感情世界的漫漫長夜裏,一點稀疏的星光在乍明乍滅而已。
這是我最近想起有關「Nostalgia」這個字的小故事。但愛因斯坦對我來說,畢竟是太大也太遠了。
「Nostalgia」這個字,我忘了是甚麼時候學的,但印象最深的是來自哈佛的日文課。老師要我們在學期結束時大家表演。我要朗誦日文詩,所選的一首叫〈馬戲團〉,詩中就有「Nostalgia」這個字。在這首日文詩裏,「馬戲團」與「鄉愁」二字用的既不是漢字,也不是日文平假名,而是直接借用英文的外來語片假名。所以,「囗」(Circus)與
「囗」(Nostalgia)二字,每一個英文原文中婉轉帶過的字音,在日文裏都成了明顯的音節。我聽到自己的聲音在空氣中微微顫抖的同時,想起馬戲團巡遊賣藝,流徙四方,又哪有固定的家可言?在笑聲處處的馬戲棚內外,似乎只有快樂,但竟然生出「浮草」之意(是日文漢字的浮草)。那天我只是在想:人類如何浮在人生長河的水面上,又如何似是自在卻不由自主地隨波逐流。這算第二個與「Nostalgia」有關的小故事罷。
離開波士頓,到了香港以後,這幾年我教中國古詩的翻譯,總是從李白的〈靜夜思〉開始。凡是中國人,似乎就沒有不知道這首五言絕句的。簡單得好像都不覺得它該是一首詩,容易得更像不論誰都以為自己也作得出來。譯成英文的作品隨意找來一看,就是十幾家。
諸家大作不是直譯多些,意譯少許;就是直譯少些,意譯多些。比如翟理斯(HerbertGiles),羅威爾(AmyLowell),及賓納(WitterBynner)等的譯作所含直譯或意譯的成分,程度上各有不同。而我最佩服的是翁顯良的譯作,完全是意譯。詩而完全意譯,固屬自由,但極吃力;何況他又不講格律,甚至可以說以散文入詩。也許翁顯良有李白的瀟灑丰神與豪爽懷抱,因而譯詩可以達到脫胎換骨的境界。他是這樣譯的:
床前明月光, Asplashofwhiteonmybedroomfloor.Hoarfrost?
疑是地上霜。 Iraisemyeyestothemoon,thesamemoon.
舉頭望明月, Assceneslongpastcametomind,myeyesfallagain
低頭思故鄉。 Onthesplashofwhite,andmyheartachesforhome.
譯文讀來已使人佩服,至於「靜夜思」這一詩題,所有譯家都在「靜夜」(tranquilnight)或「思」(thoughts)上打轉,而翁只將其譯成一字,即「Nostalgia」!這真是,也只能是神來之筆,可遇而不可求矣。「意態由來畫不成」,翁顯良從哪裏找來的畫筆與顏料,畫成如此淡雅而又自然的作品。
翁顯良是誰呢?原來是來自香港!他生於一九二四年,一九四○年進入香港大學。大概時間與遭遇均與張愛玲差不多罷!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他返回大陸,就讀於中山大學,於一九四七年畢業。四八年又回到香港,四九年再赴廣州,從此漂泊在內地。經過那非人間的十年以後,才在人生昏黃時,趕着譯了一些詩。以後,不知怎麼就無聲息地凋零了。
這三個互不相干的小故事,都把「Nostalgia」這個字,深印在我這片葉子上。我就借這片葉子上所題的「ForMutualNostalgia」——「為彼此的鄉愁」,作為這本書的書名,獻給那些正在懷鄉、或在憶舊,彼此的、或共同的,滿天顫抖的、或已化為泥土的萬千秋葉,與一望無際、萬古銷沉的蕭瑟秋天。
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