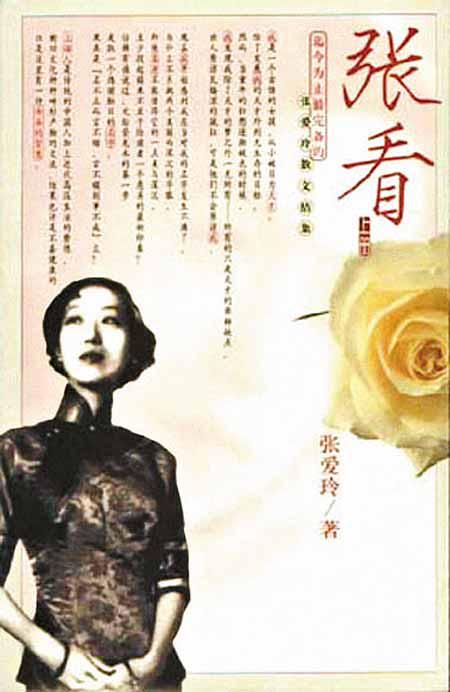《張看》是張愛玲的小說散文集,1976年由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內收〈天才夢〉一篇,有附言曰:「〈我的天才夢〉獲《西風》雜誌徵文第十三名名譽獎。徵文限定字數,所以這篇文字極力壓縮,剛在這數目內,但是第一名長好幾倍。並不是我幾十年後還斤斤較量,不過因為影響這篇東西的內容與可信性,不得不提一聲。」
劉紹銘
這樣一篇附言,一般「張迷」看了,大概也不會在意。〈天才夢〉是絕好散文,結尾一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膾炙人口。至於文字為什麼要如此壓縮,第一名的作者為什麼可以超額,除了「張學」專家,普通讀者諒也不會深究。
十八年後,張愛玲舊事重提。她拿到了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的特別成就獎,因寫了〈憶《西風》〉感言。此文讀來竟有「傷痕文學」味道,值得簡述一次。1939年,張愛玲初進港大,看到上海《西風》雜誌徵文啟事。她手邊沒有稿紙,乃以普通信箋書寫,一字一句的計算字數,「改了又改,一遍遍數得頭昏腦脹,務必要刪成四百九十多字,少了也不甘心。」
不久她接到通知,說徵文獲得首獎。但後來收到全部得獎者名單,第一名另有其人,她排在末尾。根據她的憶述,首獎〈我的妻〉「寫夫婦倆認識的經過與婚後貧病的挫折,背景在上海,長達三千餘字。《西風》始終沒有提為什麼不計字數,破格錄取。我當時的印象是有人有個朋友用得着這筆獎金,既然應徵就不好意思不幫他這個忙,雖然早過了截稿期限,都已經通知我得獎了。」
張愛玲1995年逝世。1994年十二月發表的〈憶《西風》〉是她生前見報的最後一篇散文。她決定舊事重提,自覺「也嫌小器,……不過十幾歲的人感情最劇烈,得獎這件事成了一隻神經死了的蛀牙,所以現在得獎也一點感覺都沒有。隔了半世紀還剝奪我應有的喜悅,難免怨憤。」
〈憶《西風》〉發表後,「張迷」看了,莫不為她的遭遇感到憤憤不平,但事隔半個多世紀,張愛玲只憑記憶追述,「片面之詞」,可靠麼?陳子善教授終於找到《西風》有關徵文和徵文揭曉的兩份原件,寫了〈《天才夢》獲獎考〉一文,給我們揭開謎底。跟張愛玲的敘述比對過後,發覺她的記憶果然有誤。徵文的字限不是五百字,而是五千字以內。第二個跟她記憶不符的地方是她拿的不是「第十三名名譽獎」,而是第三名名譽獎。不過她「叨陪榜末」倒是事實,因為名譽獎只有三個。
張愛玲把五千看成五百,已經糊塗,把名譽獎看成首獎,更不可思議,不過這件「公案」既然有原件作證,我們只有接受事實:張愛玲的「傷痕」,原是自己一手造成,也因此抱憾終生。撇開這件「風波」不提,張愛玲〈憶《西風》〉最意味深長的一句話是:「我們中國人!」這句「對自己苦笑」說的話,緊接「我當時的印象是有人有個朋友用得着這筆獎金」。未說出來的話是,這種偷天換日、假公濟私的把戲,原是「我們中國人」優為之的事,因此她只好認命,「苦笑」置之。
如果她本該拿首獎後來竟排榜末確是《西風》編輯部營私的結果,那麼我們的確可以把這種「調包」行為看作國民劣根性一顯例。張愛玲自小在陰暗的家庭長大,父親抽大煙,吸毒,花天酒地,動不動就要置兒女於死地。中國文化的陰暗面、中國人的劣根性,她比誰都看得清楚,難得的是她「逆來順受」。如果不是《中國時報》發給她特別成就獎,挑起了她的傷痕,諒她也不會作出「我們中國人」的興嘆,因為張愛玲也接受了自己到底也是中國人這個事實。不妨引〈中國的日夜〉(1947)作為參考:「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快樂的時候,無線電的聲音,街上的顏色,彷彿我也都有份;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總之,到底是中國。」
我細讀〈憶《西風》〉,想到鄭樹森教授在〈張愛玲與《二十世紀》〉介紹過張愛玲的英文著作。《二十世紀》1941年在上海創刊,主編克勞斯.梅湼特(KlausMehnert)是德國人。
這本英文刊物「鎖定」的讀者對象是滯留亞洲的外籍人士。張愛玲於1943年開始在《二十世紀》寫稿,首次登場的“ChineseLifeandFashion”(中國人的生活和時裝),後來自己譯成中文,以〈更衣記〉為題發表。鄭樹森說這篇作品看不出翻譯痕跡,只能說是中文的再創作。
因為張愛玲說過「我們中國人!」這句話,我對她刊登在《二十世紀》的文章馬上感到濃厚的「職業興趣」。學術文章就事論事,讀者對象無分種族國界。但散文難免涉及一己的愛憎和是非觀。對象如果是「外人」,那麼說到「家醜」,要不要直言無諱,還是盡力「護短」?以洋人市場為對象的「通俗作家」,因知宣揚孔孟之道的話沒人愛聽,為了讓讀者看得下去,不惜販賣奇巧淫技。纏足、鴉片、風月怪談等chinoiserie,一一上場。借用十多年前流行的說法,這就是「魔妖化」(demonize)中國。
張愛玲在上海時期靠稿費生活,如果英文著作有「魔妖化」迹象,可理解為生活所迫。但她沒有走「通俗」路子。在〈中國人的宗教〉一文,她談到中國的地獄:「『陰間』理該永遠是黃昏,但有時也像個極其正常的都市,……。生魂出竅,飄流到地獄裏去,遇見過世親戚朋友,領他們到處觀光,是常有的事。」
把目蓮救母的場景說成「旅遊勝地」,可見二十四歲的張愛玲,還不失孩子氣。但她一本正經給洋人介紹「我們中國人」的各種「德性」時,確有見地。最能代表她在這方面識見的,是〈洋人看京戲及其他〉。她一開始就說明立場:
多數的年青人愛中國而不知道他們所愛的是一些什麼東西。無條件的愛是可欽佩的──唯一的危險就是:遲早理想要撞着了現實,每每使他們倒抽一口涼氣,把心漸漸冷了。我們不幸生活於中國人之間,比不得華僑,可以一輩安全地隔着適當的距離牽繫着神聖的祖國。那麼,索性看個仔細罷!用洋人看京戲的眼光來觀光一番罷。有了驚訝與眩異,才有明暸,才有靠得住的愛。
張愛玲初識胡蘭成時,有書信往還。胡蘭成第一封給她的信,「竟寫成了像五四時代的新詩一般幼稚可笑。」張愛玲回信說:「因為懂得,所以慈悲。」《西風》事件對她是一個負面的陰影,可是因為「懂得」,日後才能說出「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
用洋人看京戲的眼光看中國,看到的是什麼景象?雖然她說京戲裏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國,也不是古舊中國的任何階段,但她對中國民風民俗的觀察,今天看來一點也不隔膜。且看她怎麼說中國人沒有privacy的觀念。「擁擠是中國戲劇與中國生活裏的要素之一。中國人是在一大群人之間呱呱墮地的,也在一大群人之間死去。……中國人在那裏也躲不了旁觀者。……青天白日關着門,那是非常不名譽的事。即使在夜晚,門閂上了,只消將紙窗一舐,屋裏的情形已就一目了然。」
她認為因為中國人缺少私生活,所以個性裏有點粗俗,因此除了在戲台上,「現代的中國是無禮可言。」這些觀察,既尖銳,也見膽識,但最教人佩服的還是她對魏晉任誕式人物的評論:「群居生活影響到中國人的心理。中國人之間很少有真正怪癖的。脫略的高人嗜竹嗜酒,愛發酒瘋,或是有潔癖,或是不洗澡,講究捫虱而談,然而這都是循規蹈矩的怪癖,不乏前例的。他們從人堆裏跳出來,又加入了另一個人堆。」
張愛玲向洋讀者介紹「吾土吾民」,依書直說,毫不煽情。沒有抹黑,也不美化。如果中國人愛群居,四代同堂,也沒有什麼不對,用不着向洋人賠不是。這種不亢不卑的態度,梅湼特極為欣賞。他在編輯按語中指出,張愛玲「與她不少中國同胞差異之處,在於她從不將中國的事物視為理所當然;正由於她對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國人詮釋中國人」(鄭樹森譯文)。
張愛玲把自己的英文作品翻譯成中文,大概她認為中國讀者更有理由近距離細看她筆下的中國,好讓他們「懂得」。〈中國的日夜〉以她的一首詩結束: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國土。
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補了又補,
連了又連的,
補釘的彩雲的人民。
詩成於1947年,《西風》徵文的風波顯然沒有影響她對自己到底是中國人身份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