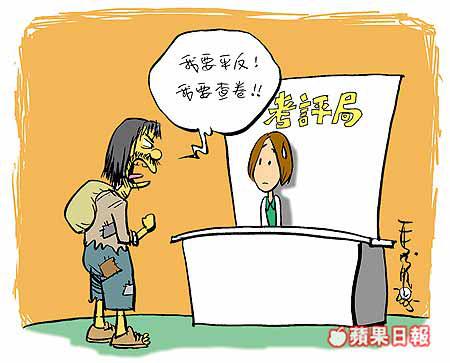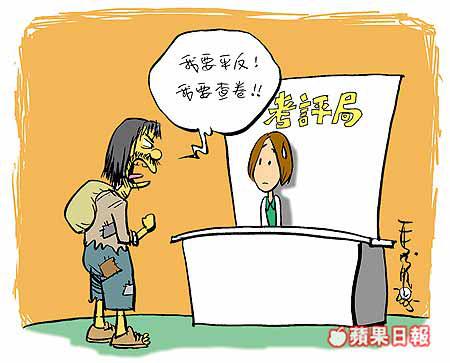
前天《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文章,指摘台灣當局漠視抗戰勝利六十周年,說陳水扁發表的「紀念專文」,連日本兩字都不敢提,談到抗日戰爭,阿扁只用「終戰」而不是「勝利」的字眼。文章認為,抗日戰爭對台灣來說,有極為特殊的意義,因為台灣在「落入日本的魔爪」五十年後,終於「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
這是中國大陸人對台灣人處境的自以為是的思維。實際上,抗戰時是台灣人陷入身份認同嚴重錯置的時代。對許多被日本徵召入伍的台灣兵來說,日本投降就得隨着日軍留在原地等候繳械,是「終戰」還是「勝利」真是說不清。戰後國民黨軍隊接收台灣,一些「台籍日本兵」又被強拉去當壯丁,成為「台籍國府兵」,被迫參加國共內戰。一位參加國共內戰的台籍國府兵徐騰光,在徐蚌會戰中被共軍俘虜,後送往朝鮮打韓戰,韓戰結束又因他的台籍身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中共專政機關問他:「你是國民黨軍官,又是台灣人,是不是潛伏在大陸做間諜。」他在大陸受了大半輩子的罪,十多年前回到台灣,連聽閩南話都吃力。
戰時台灣人是有投身到大陸參加抗戰的。以抗日為職志的少年李友邦,前往大陸抗日,卻被福建省政府以「敵國人民」處置,關進武夷山下的「台民墾殖所」。二戰後,曾加入抗戰的李友邦,被國府質疑為「匪諜」,以「叛亂罪」槍決,死時才四十六歲。
台灣人的身份,在抗戰時可說「裏外不是人」。他們加入抗戰的「台灣義勇隊」,被疑為日軍「間諜」;他們參加協助日軍的「高砂義勇隊」,在日軍中又被歧視,地位低於日本人和琉球人;他們被日軍徵召到大陸,大都擔任被視為「幫兇」的日軍繙譯;他們有被徵召到南洋當「拓南戰士」的,有到大陸當「台籍女護士」的,有被拐騙賣身的「台籍慰安婦」,有遠赴日本造飛機的「台灣少年工」及「台籍神風特攻隊員」。
在二戰中戰死的台灣人,因為不是為中國而捐軀,國民政府不願接受他們的靈魂,於是三萬名台灣人的靈位只能被安置在日本的靖國神社。對許多台灣人來說,連靈魂都未能「回到祖國的懷抱」。
台灣人到大陸參加抗日、甚至參加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並不是只有個別人遭到厄運,而是絕大多數人都被懷疑為日本、台灣的特務,只因「非我族類,其志必異」。連台盟領袖、中共黨員的謝雪紅也在大陸被整肅。
戰後「重新回到祖國懷抱」的台灣,遭到的是比日治時代更不如的缺乏法治的國民黨統治,又一直受中共威脅着要以武力攻台。若不是受到美軍的保護,台灣哪裏有戰後的繁榮?只怕淪為比海南島更不如的貧困地區了。
今天台灣許多人的「親日」,是因為歷史上台灣人從一個「魔爪」落到另一個、再一個的「魔爪」,也因為現實政治中「美日安保」對台灣的保護。
對二戰時台灣人的身份錯置,必須要理解與寬容。這是紀念二戰結束最應記取的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