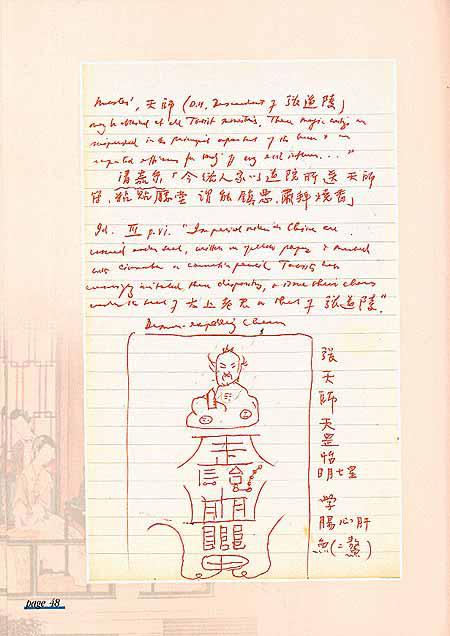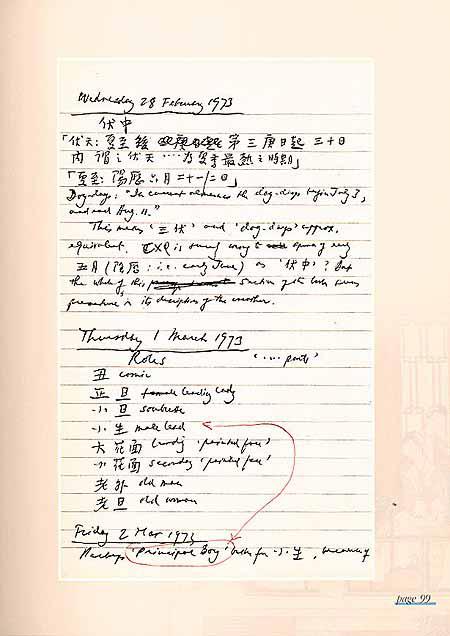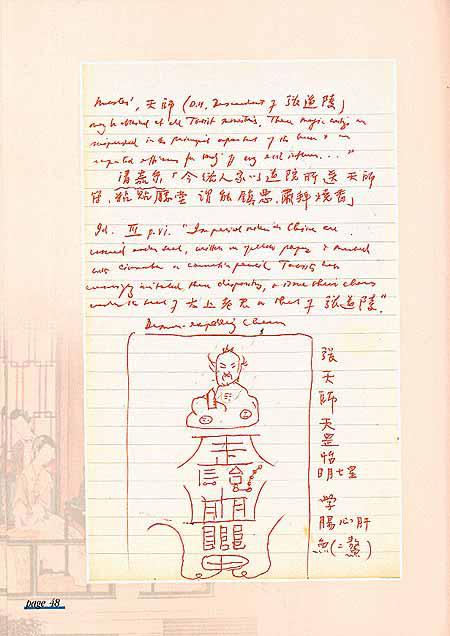
我在嶺南大學中文系講授傳統和現當代小說多年,每次上課一有機會,就苦口婆心的勸告同學,一定要爭取機會學好英文。這種行徑,迹近吃裏扒外,但對此絕無歉意,今後還會繼續傳福音。因為事實擺在眼前,英語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強勢無可取代。這是上青雲路的天梯。為家為國為己,一定要把英文學好。同學說迷上張愛玲作品,我就抓緊機會問:蒼涼的手勢,英文該怎麼說?他們說不出來,我就寫在黑板上:adesolategesture。「蒼涼的手勢」,說法別有一番滋味,過目不忘,因此我相信同學對這句話英文的dynamicequivalent,也特別容易上心。
劉紹銘
美國人做事,力求苦中作樂,什麼都講fun。吃喝玩樂貪求開心過癮不在話下。「啃書」本該正襟危坐,但他們一樣有辦法讓你覺得其fun無窮。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在美國讀書時,最耳熟的一句電視廣告是doubleyourpleasure,doubleyourfun。畫面上是一對雙胞胎姐妹媚眼如絲,一搖一擺的唱着。賣的原來是白箭牌口香糖。初級語文課本,插圖彩色繽紛,目的就是要讓孩子在唸書時有fun,不致一打開書本就被各種清規戒律悶倒。
林語堂當年教人看電影學英文,頗有新意,但知易行難。幽默大師的年代,沒有DVD。一部電影要「聽」多少遍才聽出語言的味道來?《北非諜影》堪富利.保加那句經典名言,playitagain,Sam,英文有基礎的,應該聽出此話斷腸的辛酸。可是初習英文的,如果只看這張片子一次,恐怕還不會記得這「經典」的完整句子。看電影學英文確是fun,但如果要收效果,手上得有電影對白的「文本」對着來唸。這也是說,錄影機和DVD不可或缺,因為你要一再觀賞,才能記誦其中對白。
「聽歌學英文」,也是根據thepleasureprinciple衍生出來的原理。看電影、聽歌都是快樂的事。五十年代的香港,披頭四還未見踪迹,流行的是「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如怨如慕的心曲,如DearJohn或IWenttoYourWedding等。哀艷纏綿的,有MoonRiver,UnchainedMelody和PutYourHeadonMyShoulder等等。還有SmokeGetsinYourEyes吧。事隔多年,這些「靡靡之音」曲詞,大部份記憶猶新。年紀輕,記憶力好,當然是原因,但最大的關鍵應該是這些歌詞,把「少年的我」心中要說,但不知從何說起的話都說了出來。這些流行曲因此是我們的代言人。
「聽歌學英文」,跟看電影學英文的道理一樣,要收效益,得有文本對照。流行曲的歌詞,一般都簡單明瞭,不會出現problematize這類艱深的字眼。不過,對初學英文的人來說,像TheGreatPretender這首歌,要聽懂,有些字可能要查字典。由此可知,聽歌儘管有fun,基本工夫還是要做的。但因要「啃」的文本是自己的興趣,唸起來就舒服多了。
學英文,如果選的課文適合自己興趣,會唸得其樂融融。大學程度的同學,大可按自己所好挑選名家作品來唸。莎劇自然是英文至善之境,怕的是生字太多,行文usage跟今天的英語隔了好幾個世紀,同學看十行莎劇,用在查字典、參看注釋的時間往往就是一個晚上。書「啃」得這麼吃力,還有什麼fun可言?
因此我想到除了看電影和聽歌外,還可以考慮通過翻譯學英文。要投自己所愛,不妨選擇中譯英的文本。你喜歡李白的〈長干行〉?好啊,試抄前四句,看看英文怎麼說:「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
Whilemyhairwascutstraightacrossmyforehead
Iplayedabouttheforestgate,pullingflowers.
Youcamebyonbamboostilts,playinghorse,
Youwalkedaboutmyseat,playingwithblueplums.
這是美國大詩人EzraPound的譯文。Pound對中文只是一知半解,靠的是ErnestFenollosa留下來的一些筆記,但限於篇幅,這裏不及細表。總之,以英文論英文,Pound是大家,難怪KennethRexroth譽此譯詩為二十世紀中用「美式英文」(American)寫成的十來首最偉大詩作之一。
讀Pound的譯文為什麼是fun?因為原詩是李白的作品,你本來就喜歡。第二,因為譯文讀來舒服。以大學生的英文程度言之,全詩要查字典的生字不多,usage也相當現代,不會予人隔閡之感。「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AtfifteenIstoppedscowling,/Idesiredmydusttobemingledwithyours。我們今天說的,也是這種英文。
要選翻譯文字作英語讀本,首先要考慮的是自己對原文是否有感情。現在假定你對《紅樓夢》有偏愛,我們試以第一回甄士隱解注〈好了歌〉為例吧:「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Insuchcommotiondoestheworld'stheatrerage:
Aseachoneleaves,anothertakesthestage.
Invainweroam:
Eachintheendmustcallastrangelandhome.
Eachofuswiththatpoorgirlmaycompare
Whosewsawedding-gownforanotherbridetowear.
譯文是牛津大學漢學榮休教授DavidHawkes手筆。他的譯文不能拿來作翻譯範本,因為他執筆時沒有想到拿自己文章用作「漢英對照」。我引「翻譯學英文」的例子,着意的先是英文,翻譯是次要的考慮。從上面引文可以看到,Hawkes譯文不跟隨原文syntax的次序。把「反認他鄉是故鄉」譯為Eachintheendmustcallastrangelandhome,在我看來與原意有出入。但這些翻譯上是否失當的枝節,無損學英文的大前提。英譯《紅樓夢》有多家,以英文功力而言,無人比得上Hawkes的TheStoryoftheStone(《石頭記》)。
《紅樓夢》是小說,對白特別精彩。以學習「實用英語」的眼光看,研究對白的翻譯比研究中詩英譯更有價值。我們且看鳳姐兒說起英文來是什麼一種嘴臉。第六回周瑞家的引進劉姥姥拜見鳳姐,這位伶牙利齒的「大內」女管家笑着對村婦說:「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疏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裏沒人似的。」
“Relationsdon'tcometoseeusmuchnowadays,”saidXi-fengaffably.“Wearegettingtobequitestrangerswitheverybody.Peoplewhoknowusrealizethatitisbecauseyouaretiredofusthatyoudon'tvisitusoftener;butsomespitefulpeoplewhodon'tknowussowellthinkit'sourfault,becausewehavegrowntooproud.”
Hawkes這段譯文,很是貼切,拿來作漢英對照翻譯範本,既可學英文,也可研究翻譯,可說相得益彰。要通過翻譯學英語,最理想的版本是「雙面內文」:一打開書就看到原文和譯文對照,句子和段落的次序也各就各位。就我所知,有計劃、有資源(因為有市場)繼續出版這種雙語文學著作的機構僅得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面世的有鄭樹森教授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學中英對照系列」,編輯委員會由葛浩文(HowardGoldblatt)、金介甫(JeffreyC.Kinkley)、和譚國根三位教授組成。創業的「首本戲」是白先勇的《台北人》,跟着下來的有魯迅、巴金、沈從文、茅盾、老舍、蕭紅、梁實秋、周作人、林海音、阿城、和高行健等人的作品。我上面說過,要通過翻譯學英文,首先要對「被翻譯」過來的作者有感情上的認同。如果原文也看不下去,那有興趣看翻譯?
這系列的譯者,既能通過四位編委的審查,自然是一時之選。其中英文特別出色的有三位,以字母排列分別是譯蕭紅的葛浩文(HowardGoldblatt)、譯阿城的詹納爾(W.J.F.Jenner)和譯周作人的卜立德(DavidE.Pollard)。這三位漢學家,英文寫得有個性、有氣派、有文彩。我讀他們三位的譯筆多年,覺得就文字論,他們本身已是優秀的散文家。
篇幅所限,不能在這裏一一舉例說明三位的造詣,只希望有心的讀者自己找譯文去體會了。葛浩文譯的是蕭紅六個短篇小說。詹納爾譯阿城的《棋王》。卜立德譯周作人三十篇散文。卜立德選譯周作人,因得在同一時間、同一文本中盡顯漢學家、翻譯家和散文家三種不凡的身手。熟悉周氏作品的讀者都知道,這位善寫草木蟲魚的知堂老人,行文時愛引經據典。要細讀原文,已花功夫,更何況譯成得體的英文?〈苦雨〉中有「樑上君子」一語。好卜立德,他不慌不忙,氣定神閒的招呼他們一聲gentlemenoftheburglarfraternity。這是aseamlesstranslation,既與原意湊合,也幽默得可以。這也是上好的英文。
老友弦多年前為《聯合報》編一特輯組稿,來信告訴我為了拉朋友寫文章,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這譬喻精彩。學英文也要「喪心病狂」才能成事。看電影、聽歌、讀翻譯,都是一條門路,但不是捷徑。字典還是要翻閱的。書還是要「啃」的。這是我給班上同學說的「苦口婆心」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