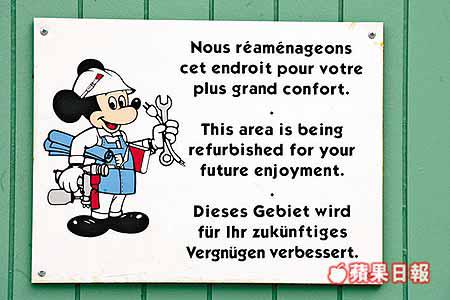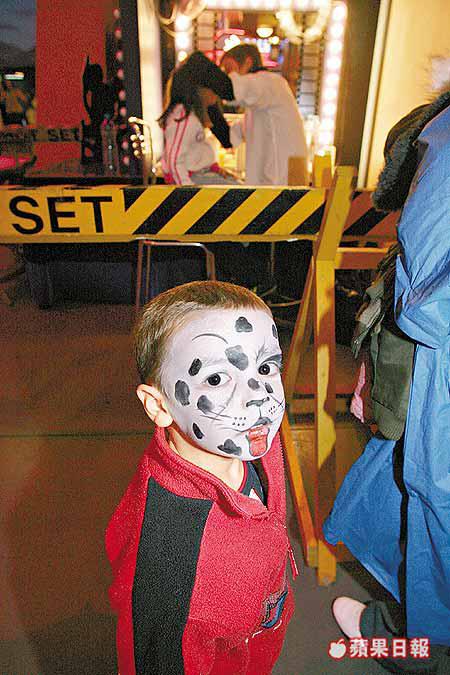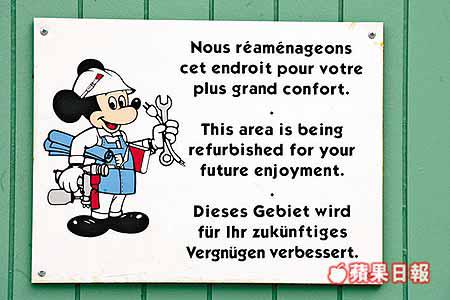
美國流行文化過去大半個世紀無堅不摧,強勢席捲全球;一如荷李活電影、麥當勞快餐,迪士尼作為美國文化的表徵(美國前總統列根形容是國寶),它的卡通人物、電影、音樂和主題公園,不但是美國幾代家庭兒童的集體回憶,也成為世界不同地方孩子最早認識簡單化了的善惡、美醜和是非的媒介。
迪士尼引申而來的文化、勞工和環保等議題,使它成為知識界和關注團體長期批判的對象。環保組織反對它賣魚翅;社會服務團體希望它回饋社會。影響力愈大、責任就愈大,公眾將要求擁有不少特權的香港迪士尼,履行更多企業責任。 記者:陳沛敏迪士尼直擊(20之5)
米奇老鼠不一定人見人愛,當年巴黎的迪士尼樂園開幕,法國總統米特朗甚至拒絕到訪,傳媒引述他說:「那不是我那杯茶。」在巴黎街頭好不容易找到會說(或肯說)英語的法國人,大都對迪士尼印象欠佳;在樂園內,來自歐洲其他地方的遊客還好,問法國本土人為何來玩,他們多會冷冷呼出煙圈,淡然說:「只為帶孩子來。」
迪士尼不但受到部份法國人冷待,它的成功也令「迪士尼化」對社會影響,成為學術界和文化界關注的課題。他們認為迪士尼除將主題性消費模式推至全球,其慣用簡化、煽情和公式化的手法,將真實世界「消毒淨化」成沒有對立、分歧和多元性的糖衣假象。
主題旅遊影響全球
在九十年代初,迪士尼公司有意興建名為「迪士尼的美國」(Disney'sAmerica)的主題公園,立即遭歷史學家和環保人士群起反對,結果計劃被迫擱置。歷史學者擔心,迪士尼會過份簡化及淨化像美國原住民、奴隸制度等較複雜和敏感的題材,一如奧蘭多華特迪士尼世界內Epcot的「美國歷險」和神奇王國的「總統館」一樣。
在本港,九九年與友人合著《迪士尼不是樂園》的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葉蔭聰指出,迪士尼不純粹是主題公園,它還代表一種旅遊開發和城市發展形式,會改變人們對一個地方的認知和了解,「現在全世界都作主題公園式發展,例如去韓國旅行會去大長今村。」
「以前去一個地方旅行,你會去了解當地人嘅生活、文化,但係𠵱家去當地嘅主題公園,其實係透過大企業塑造嘅旅遊經驗……將來嚟香港嘅人都可能會係咁。」葉蔭聰指出,從本土文化角度,迪士尼對生活環境帶來微妙變化,例如一直叫作陰澳的地方,突然變成「欣澳」,「過多幾十年,可能會無人會記得有個叫陰澳嘅地方。」
微妙改變社會文化
由一群大專院校師生組成的「獵奇行動」,則準備長期監察樂園對本港社會和文化景觀帶來的影響,包括勞工、環境、經濟、文化教育、官商勾結、壟斷版權、性別議題、社會平等及全球迪士尼化;也有學者計劃研究消費者如何受到影響和改變。迪士尼樂園開幕,不只是為本港帶來一個新興的旅遊點,也將成為一個影響社會多方面的現象。
《玩盡全球迪士尼》明日起轉刊在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