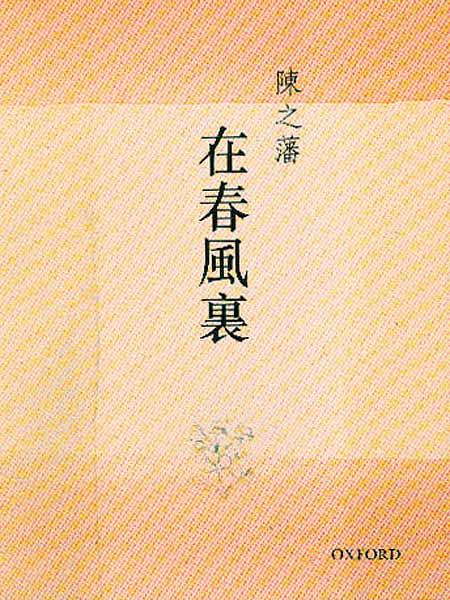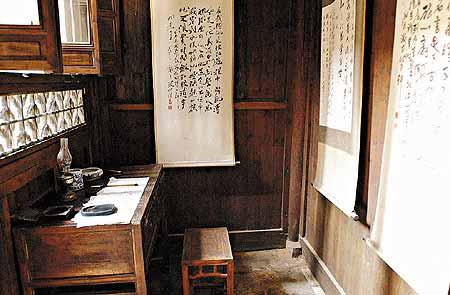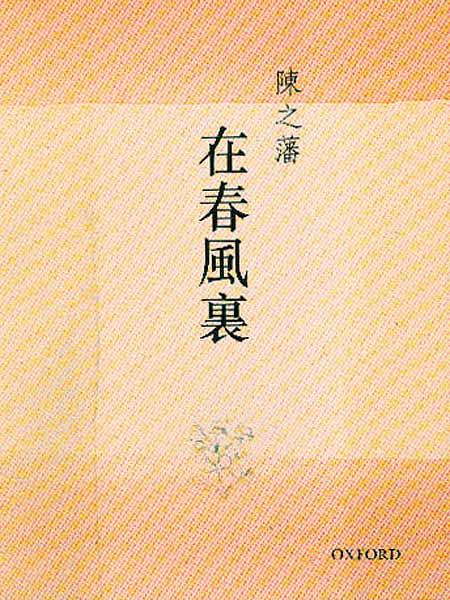
陳之藩 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榮譽教授
陳之藩簡介
1925年生,北洋大學電機系學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科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副研究員,休士頓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波士頓大學研究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榮譽教授。著有電機工程論文百篇,《系統導論》及《人工智慧語言》專書二冊;散文有《蔚藍的天》、《旅美小簡》、《在春風裏》、《劍河倒影》、《一星如月》、《時空之海》、《散步》等;選入香港中學中文教科書者,有〈寂寞的畫廊〉等四篇。
《在春風裏》這本小書的後半是我聽到胡適之先生突然在台北逝世的消息後所寫的幾篇紀念文字。時間是一九六二年,地點在美國密西西比河邊的曼斐斯城。那時我在曼城做教授已五年了。這間大學是個教會學校,而我所教的是電機工程。
至於這本小書的前半,則是胡先生逝世的消息傳來以前那五年的作品。第一篇是〈寂寞的畫廊〉,是我在費城上了兩年半學,暑假在紐約休息了三個月,之後去了曼城,在那個小大學開始教書的前夕所作的。
如果說《旅美小簡》是在費城的散記,那麼可以說《在春風裏》是在曼城的。在此,為沒有序的《在春風裏》補一個序,為什麼這麼多年來未寫,而現在才補呢?因為從一九五五年我去美國到一九六○年他到台灣,正是胡適之先生在紐約最是冷清、最無聊賴的歲月,我才可能有與他聊天、談心、說短、道長的幸運。他是位多忙的人!這段期間之前,我在北平;之後,我在台北;各見過他一次。初次相會時間有十分鐘,因賀麟要向校長商量學生的急事而打斷;第二次談話的時間也不到二十分鐘,為副總統陳誠的造訪而打斷。兩次合在一起不過半小時。在美國,尤其我也在紐約市的三個月,我常到胡寓閒談,應以小時計了。所談的是天南地北,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複雜得不易收拾。想補於序中,遂更使此事變為艱難。
讓我回溯到半個世紀前的一九五七年,我由費城到了紐約。在曼哈頓的西城租到一間房,因距哥倫比亞大學不遠。剛放暑假,極易租到房住,我預備純休息兩三個月後再去南方的曼城。那個小大學到九月初才開學。找好了住處的當天,就去東城的八十一街去看適之先生了。
我在費城與他的通信中,他早知道我要去曼城,並且查了美國教育年鑑之類的書,知道那個小大學的情況,並且知道得相當詳細。比如曼城是美國的第十九大城,有五十萬人,那個小大學的電機系只有兩個教授等。我一進門他就問:「之藩,你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念的是什麼學位呢?有兩年半了罷?」
那兩年半中,他總是為我擔心。他不會不知我拿的是碩士學位,但是,他看到過那個小大學的聘函,不但是正教授,而且待遇幾乎是讀完了博士學位也不見得能拿到的薪給。舊的擔心去了,又換上新的擔心:我幹得了嗎?
我說:「是兩年半才念了個碩士。過去兩年中我每個星期日到費城的中國飯館做一天工,掙約十七元,拿這十七元吃六天也夠了。暑假在湖邊做暑期工,可掙幾百元,交學費也差不多了。星期日的一天工好像不算什麼,由廚房到餐廳,由餐廳再到廚房,不是站,就是走,所以星期天回到學生宿舍,只是乾瞪著眼睡不著。也不知道為什麼失眠,後來才知道是在飯館打工累的。
「我原以荀子所說的『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的戡天志向來留學。哪知結果是成了孟子所說的『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他聽到這裡哈哈大笑起來,轉了個話題說:「杜克大學有回信沒有?」因為我曾請他為我寫一封推薦信給杜克大學申請獎學金繼續念博士。我說:「沒有。我窮成這樣,想先教書去。就是有獎學金與入學許可,我也不去。」胡先生於是說起杜克大學的故事來。他繼續微笑著說:「跟傅孟真可不能提杜克大學,杜克大學與英美煙草公司有很深的關係。五四以後,英美煙草公司送『五大臣』出洋。所謂五大臣,就是傅斯年等五人。傅的出洋資助者既是英美煙草公司,他認為是他一生中之奇恥大辱,所以連提都不能提。」
我則說:「您所立事業很多,有的因治病而請人暫代,比如,到上海治病讓顧頡剛暫代雜誌的主持;又如,北大校長位子在勝利接收時,您答應做校長,但因病而尚未去,曾以傅斯年暫代。我看這些暫代常出問題。傅的勇敢夠,而氣度不夠,接了北大代校長後好像先宣佈北平的北大學生是偽學生,北大的教授為偽教授,於是許多偽學生與偽教授都到紅軍佔領區去了。陳誠如不是見識不大,就是度量太小,他去東北接收,卻把『滿洲國』的軍人,稱為偽軍罷,也擠到共產黨那裡去了。連改編敵軍的度量都沒有,何況那並不是正面的敵軍,是接收的順軍。為何這樣沒有度量?這不是國家的大臣與大將所應有的態度。我說這些事後聰明的話,您不會怪我罷。」
傅、陳都是適之先生很好的朋友,兩個人也都能幹,也都尊敬他。我就問他是不是因為一位是胃潰瘍,一位是血壓高的關係?
他用左手摸著自己的右手的腕子讓我看,並且說「瘦成這個樣子」。好像是求我原諒他找人暫代的理由。我知道我說重了話,話出口也收不回來了。那天他送我到電梯口,電梯一關我就哭了。自己怪自己怎麼可以這樣粗暴,所對的還不是別人,是對軟心腸的胡先生。
有一天,我的房東太太看到我從外邊回來說:「有位胡先生給你打電話,他說的英文又禮貌又好聽。他說你如五時前回來,就去他那裡,他邀你去吃飯;如五時以後回來,就給他個電話。」我立時去了。不知為什麼,那天胡先生想邀我去吃飯館。我們一同散步去,過街時,等紅燈,剛換燈時我先行。我知道胡先生絕對不讓人在旁邊攙他,我剛來時不知道,剛一攙扶他,他就用力甩開,那一甩帶著怒氣。所以過街時,我先行。他說:「不要太忙,有時卡車想煞車也煞不住,寧稍等。」那一天,回寓後他特別送我一大本《聖經》說:「你看看。」不遠的從前,他送過我一本《丹諾自傳》、《孟肯文集》等,不是無神論者,就是達爾文主義者。他這次又送我一本《聖經》。也沒有說什麼,大概是擔心我到了教會大學會與人家鬥口舌起衝突,而我對《聖經》太無知識。今日回想起來,我所去的那間大學現在已擴充為基督修士大學(ChristianBrothersUniversity)。前幾年我在香港還看到一本小英文書,是甘地的孫子在那裡做訪問學者時寫的,大概是宣傳他祖父的不合作主義。
這都是最近的事。當年,我帶著胡先生送我的《聖經》,初到那個小大學時,我才知道我落到另一種文化裡。比如,校長教數學兼當工友。我有時找校長,校長正在搬磚鋪路。他興沖沖地對我說,草地上在學生走出痕跡的地方鋪上圓的磚,他們就會走磚了。不然,他們就只走草地,踏得亂七八糟。比如,修士們不掙一文錢,出門的車費二毛五,也要向上級要,而把學生學費所收的錢,幾乎全給了俗世的教席。我暗自驚訝,而絕對的由不信到不懂。他們是從不傳教的,哪裡有辯論宗教的可能。托馬斯修士後來升到大教區當主管,管十幾個中學、大學,常飛來飛去的。有一次在巴鐵摩爾附近半空中兩飛機相撞而死了。那時我已離開修士學院,另一修士馳函告訴我的。難道在半空中兩飛機相撞,是他受苦了一輩子,與搬磚鋪路當校長所應得的報償?這類有關修士生活的後話,感動我們這些凡人尚在其次。我在胡先生逝世了多少年後,還時常想起他說的中國的文化也有些優點,比方「淡薄的宗教」。所以,五四以後,國立的大學獨沒有神學院。我看到修士的苦修,常感覺慚愧得無地自容。我曾問這個修士,那個修士為什麼一家兄弟姊妹七人都當神職。他立即說:「一棵樹怎會生出不同的果子?」這是菲利普修士的話。也有半路出教的,再見面時,我始終不知如何稱呼。比如喬治修士,他還俗,有什麼不可以呢?為什麼他自己總不好意思。我在阿岡實驗所時常見到他,他總是老遠就避開。我卻因而想請教胡先生,可是他已逝世多年了。
話題說遠。我們還是回到那年的暑假。有一次,適之先生鄭重其事地問我:「之藩,你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究竟是在說什麼?」我說這不是張橫渠的話嗎?那天他鬱鬱不樂,只問我這四句話究竟是說什麼?我無辭可答。他為什麼比我還困惑呢?好像是同一天或第二天,他又問我:「之藩,你說,鵝湖之會他們講什麼話呢?朱子是什麼地方的人,陸氏兄弟又是什麼地方的人,言語不同啊!」我這倒有答案了。我說:「他們不說話,他們在開會之前作詩,會後還作詩。用作詩來表達思想、來溝通意見。律詩是不能廢的,他們所作也不是白話詩,也很少方言入詩。」適之先生聽我這類直話也聽慣了。我有機會就說律詩的不可廢,與作舊詩的並無怎麼不可。誠然,作律詩不克表達新的事物或新的思想,但慢慢來,不一定不可以。為什麼別的事都是一分一寸的努力,一點一滴的進步,而獨不以這種漸近的態度對待舊詩?他真是生氣,似乎是我在故意和他搗亂。他的著作中,我最不喜歡,可又很愛參考的即是《白話文學史》及《詞選》。他為什麼誓不作古詩呢。他的《嘗試集》有多少首是套的詞牌,這是我多少年後才知道的。
他因為著《白話文學史》入了迷,也就對白話變成了篤信,絕對不再有懷疑或商量的態度。有一次,他忽然對我說:「蒲松齡與紀曉嵐都是北方人,所以都用文言寫小說。」我真是不懂寫小說用文言或白話與北方人有何關係。我也是北方人,紀是我們河北同鄉,我就喜歡《閱微草堂筆記》;山東是我們鄰省,我更喜歡《聊齋》。小說用文言,多簡潔,有什麼不好。我馬上反駁說:「紀昀說,有其事,必有其理,惟人不解耳。」我不知為什麼背出這麼一句。於是又因此引出魯迅所引紀昀批評《聊齋》的話:「《聊齋》有時仿唐人傳奇,有時像六朝志怪,而每每過於細微,作者不是本人,何從知道那麼細微的心事?」適之先生又心疼周氏兄弟了。我實在是安慰他說:「魯迅在《阿Q正傳》提起您,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提起您。前者是與您開玩笑,後者是正式接受您的《紅樓夢考證》的結論。他想起您的次數不見得比您想起他的次數少,而且正式的筆之於書。您與周氏兄弟是知音。」適之先生說:「如魯迅現在還活著,也會被殺的。」也許他說的是「被鬥」的。我已忘了是哪個字了。胡先生的文學鑒賞與批評眼光,我是異常折服的。他因為喜歡周氏兄弟的創作,所以一提起他們來,就陷入沉思片刻的狀態。我仍然說我的:「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所用的文言,有多麼簡淨,而您的《白話文學史》所用的白話,有多麼自然。」那晚的談話,有些使他不大愉快,但他總是送我到電梯口。
我在曼城已教了兩年,參加了一個讀書俱樂部,每月收到大概是從紐約寄來的、他們所選的兩本書。有一個月寄來的兩書:一是《亮於一千個太陽》,是「非小說」,及《齊瓦哥醫生》。這兩本書怎麼全是令人不能釋手的書。我大概看了幾天,又找到原來裝書的盒子,把兩本書同時寄給在紐約的適之先生。他不久就給我回信說:「《亮於一千個太陽》真是太好了。」那是說二戰前後科學研究的緊張局面,特別是物理方面雙方的鬥法。看適之先生的語氣,那書使他興奮不已。而《齊瓦哥醫生》,他說:「看不下去。」但我覺得《齊瓦哥醫生》是蘇俄革命後最好的,惟一的一本。這本書拿起來也是令人放不下,是還未出版,即遭禁令的書。從第一頁開始,有這樣的句子:「『是埋葬的誰?』『齊瓦哥。』有人如此答。『喔,是呀?』『不是他,是她!他的妻子。』『喔,還不是一樣。』」,怎麼會有這種起法,能不看下去嗎?
這本書的與眾不同處,它也寫革命的激情,但也寫激情的狂潮過後的低落;他也描人物的愛戀,但人物大都是不知所終。
我絕未想到的,是適之先生竟說:「看不下去。」我接信的當時,就想起他曾那麼努力的反艾略特。艾略特的詩固然費解與難懂與不夠通俗,艾略特的文學批評,並不是太費解啊。
以後,他去了台灣,自然又忙起來了。再接不到他的信了。卻接到台大校長錢思亮替他寫的信:「因忙或病,不能回信。」他把《亮於一千個太陽》帶到台灣去讓錢思亮看。錢在信裡說,胡先生與他都鼓勵我把該書譯成中文。我那時是可以找出時間來譯那本書的,但我未立即做,他就死了。我聽到他的死訊後,真是哭著打自己的腦袋。後悔又有何用?我能力做得到的事,而竟不做,直到現在這本書也沒有人譯出來罷。
適之先生逝世近十年,一九七一年的十一月,我在英國劍橋大學拿到哲學博士學位。老童生的淚,流了一下午。我想:適之先生如仍活著,才八十一歲啊。我若告訴他,「碩士念了兩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會比我自己還高興的。
二○○五年六月十二日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