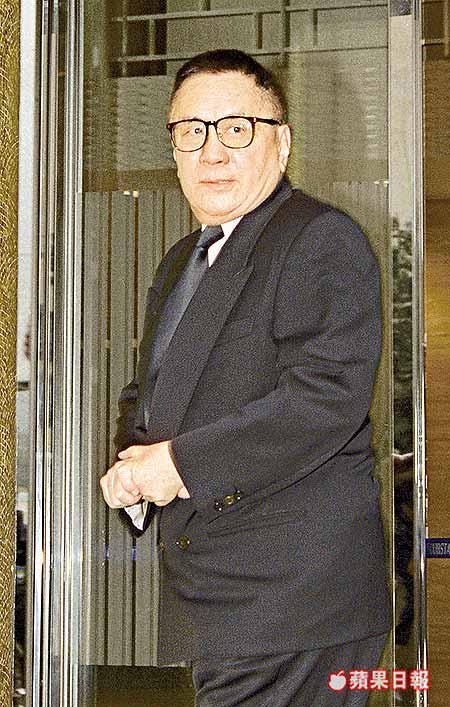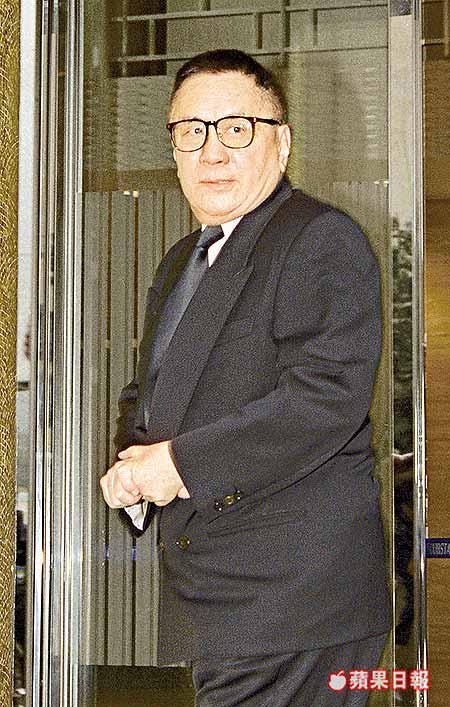
一位流行曲詞人逝世,牽動社會許多愁緒。黃霑走了,或許有人警覺:一個立法會議員逝世,隨時可以補選;一個政府高官辭職,他的副手馬上可以署任,但一個創作人走了,遺下的空缺,無從補選,也沒有人可以Acting。
黃霑先生沒有向政府要過一分錢的創作資助,他讀的是一般家長認為難有出息的文科,而且是中文系。他推動的是現代粵語流行曲,沒有寫新詩,而且把被視為低俗的文字抬升到影音工業的殿堂。他倡先開創「不文化」,公然在衣香鬢影的精英主流裏大說粗言和色情笑話。黃霑開一代風氣之先,在於他敢於做第一個,邁出第一步,在音樂和語言文化之中,黃霑是第一個「長毛」。魯迅說: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歷史卻往往由第一個敢吃螃蟹的人開創。
流行曲為甚麼只能寫鴛鴦蝴蝶的豔情,為甚麼不可以表達現代個人主義思想?黃霑在流行曲裏喊出「我係我」,有如中世紀歐洲的神權時代之末,終於出現對「人」的肯定的文藝復興。相對於歐洲五百年只以聖經和神話題材的繪畫,荷蘭畫家倫勃朗第一個「以人為本」,不再畫上帝、耶穌、聖母,而改畫夜逃的士兵、在解剖桌邊的醫生,以及自畫像。當後世的觀眾在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館看見倫勃朗用幽黯的筆觸留下他滄桑的容顏,三百多年後還能感受到一個藝術先行者的勇氣和孤獨。在宗教和神權的禁忌中,倫勃朗敢於以自畫像向四周的教士和修女發出含蓄的抗議:在這個色彩豐富的大千世界,人才是主角,人才是創造命運的主人。
武俠小說為甚麼只能寫俠客,主角一定要武功蓋世?為甚麼不可以由一個妓女的流氓兒子來做英雄?當金庸的《鹿鼎記》剛面世,華人社會為之震動,許多人不能接受主角韋小寶的人物性格:腳踏朝廷和叛亂組織的兩條船,愛賭博、喜漁色,不會武功,只憑兩片嘴皮和對黑白兩道朋友的信義安身立命,滿嘴的色情小調沒有甚麼理想,但懂得如何生存。許多人都奇怪:為甚麼武俠小說可以這樣寫?
為甚麼武俠小說可以這樣寫?為甚麼油畫可以這樣畫?為甚麼粵語流行曲的歌詞可以這樣填?為甚麼螃蟹的形相如此醜陋可怖,居然可以吃?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為甚麼不可以?」(WhyNot?)
一個時代的改革家,不論古今中外,其實就是敢於問一個問題:「為甚麼不可以?」一個開放的社會,不會因為有一個孤獨的聲音脫離了千口一音的大合唱隊而敢於問一句WhyNot,而視之如全民共誅、全國共討的十惡不赦的異端。
白人和黑人要隔離居住,男人要剃頭結辮,女人要裹腳而三寸金蓮,奴隸不享有奴隸主的人權。歷史上奪魄驚心的許多大變革,往往是由一個怯生生的人敢於舉手,問一句WhyNot開始的。當初他的問題震驚四座,震動了朝野,許多人跟他劃清界線,生怕附和他會招災惹禍。但後來他的質問引起愈來愈多的同道與共鳴,大家追隨他從另一個角度看世界,看出了不一般的風景,因此魯迅也說:世界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漸漸也成了路。
三十年來黃霑說髒話,雖然有時令人尷尬,但沒有證據顯示因為這樣一位作家的「以身作則」,提早了青少年學會說粗口的年齡,黃霑的不文集賣了六十多版,也沒有數據顯示一些讀者讀了這本書而犯下了窺浴和非禮一類的輕微風化案。粵語流行曲一度被視為靡靡之音,但這位作者身後卻得到大學問家饒宗頤先生的表揚。黃霑先生是一位潛在的社會革命家——他熱愛言論和創作自由,到了花甲之齡,卻公開表態支持二十三條立法,許多人覺得失望惋惜,但當連西遊記的孫悟空在大鬧天宮之後也終於回歸於如來的五指山,雖然中國文化的許多逆子,在「迷途」之後往往也重返道統的正軌,但孫悟空畢竟曾經另踞山頭,成為齊天大聖,有了西遊前十回的造反在前,孫悟空畢竟成就了英雄,雖然最終還是選擇了皈依。
中國的現代化荊棘滿途,由於太多人自甘於鴛鴦蝴蝶的主流,太少人敢於疾呼「說一聲:我係我」的偏鋒。在盛行吃大閘蟹的涼秋,可有想起魯迅對人類史上第一個吃大閘蟹的那位無名勇者的敬意?在涼風起天末的時候,一位流行曲的詞人乘風歸去了,原來三十年來他的作品,卻如大閘蟹一樣令人齒頰生芳。「當你見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今夜,願我們仰覽星空,想起了無數當初向上帝挑戰的勇者:倫勃朗、哥白尼、達爾文,以及在集體無聲、噤嗟眾口的歲月,敢說一句「我係我」的殉難者,是他們的星輝,為後世留下了風雲迴盪的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