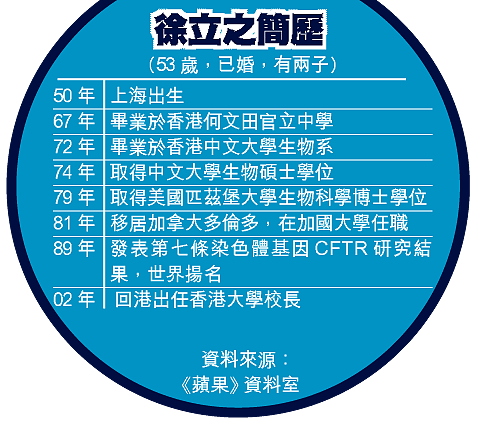
剛過去的星期二,下午三時半,八號風球高懸,我撐着雨傘到達香港大學紐魯詩樓十樓校長室,第一次面對面接觸港大校長徐立之。他應我要求,沒有因颱風取消訪問,但當被問及做校長得失,卻笑着「訴苦」:「我的時間不是我安排,約了訪問就不可以取消。」第一印象,他會輕鬆講笑話,不難相處。
談了兩個多小時,他最少每十分鐘就會有一兩句話引我發笑。狂風暴雨不時拍打窗門,呼呼聲清晰傳入耳朵,但校長室氣氛輕鬆自在。
回到報館,仔細翻聽訪問錄音帶,愈聽愈覺得徐立之像透一個人:剛上任的財政司司長唐英年。
開玩笑?兩個人一個胖一個瘦;一個是鑽石山木屋區苦學成材科學家,一個是含着銀匙出生直上雲霄生意人,驟眼看南轅北轍掛不上鈎。但容我斗膽講一句,這兩個上海人部份基因似得不能再似。 記者:李慧玲
上海出生、香港長大,然後在加拿大闖出名堂的徐立之,去年九月回歸香港,出任香港大學校長,接替因鍾庭耀事件下台的鄭耀宗。當時,港大這間百年老店,正經歷前所未有的風雨飄搖。情況與臨危受命、接替梁錦松做財政司司長的唐英年,不謀而合。
但徐立之與唐英年相似之處,豈只這些。
徐立之對自己作為港大校長的定位,謙卑得不能再謙卑:「大學校長除了是一個職銜,就是大學一分子。以前校長是領導、是家長,甚麼都由他處理,但現在不是,現在應該一齊走。做校長的,要聽意見,爭取認同。」
這番說話,何其耳熟。幾個星期前,剛上任的唐英年便說過,不是他領導香港解決財政赤字,他會與市民一起想方設法解決財赤。
徐立之強調自己「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校長」。必須承認,他和唐英年都沒有君臨天下的氣派。他們不是一站出來就壓住場面的領導,教人屏息仰望。但跟他們同場,沒有壓力,蠻舒服。
訪問期間,聽徐立之重複最多的詞語是「溝通」、「加強溝通」:與學生溝通、與教職員溝通、與商界溝通、與傳媒溝通、與社會溝通,還要與珠三角溝通。三個月前,他特別新聘一個新的傳訊總監,銳意加強校內溝通;做了校長一年,每個院系也親自到訪過最少兩次。
他也落力在港大推銷這一套。未來一年,他會安排學生到珠三角實習聯絡,也鼓勵教授與當地合作做研究。稍後,又準備向教職員提供面對傳媒技巧培訓,為教職員打開走向社會的大門。
「大家要知道社會需要,也要打開自己讓人知道。港大學術地位好高,但卻沒有向社會充份交代……可口可樂品牌最大,為甚麼還做廣告?就是要makesure人家知道他們的好。」
徐立之重視溝通也擅長溝通。用徐自己的話,他的優點是肯聽,也肯講;我現場還感受到的,是他願意遷就。食飯是一個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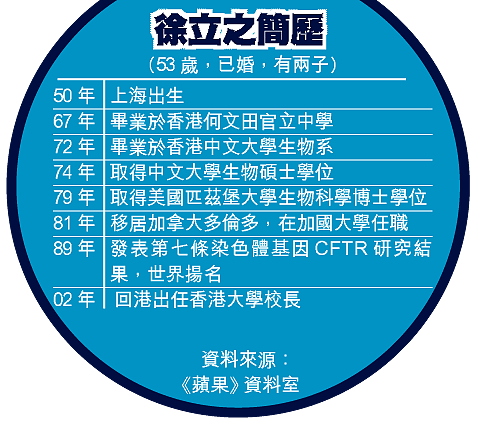
是他主動提起香港食飯文化。我問他回港一年,覺得港、加有何分別?他答:「食飯文化,香港跟西方很不一樣。」
「外國,食飯是好好享受的時候,不是去工作,不是後面跟着一件事情。我叫你食飯就是去食飯,不是有甚麼事情,不是要談甚麼或者討論某個project。在外國,今晚大家食飯,講明不會說公事,『邊個喺枱面講公事,唔該你走』。」
「但這裏好多(公事飯局),工作與食飯『撈埋』,聯絡感情一定要食飯。社交場合認識了,握握手,講兩句,要討論甚麼就吃飯,不是在辦公室談。上辦公室拜會,只是禮貌。」
一個多星期前,徐立之還見識到香港人另一門食飯的學問。他在食肆食飯,結帳時才知道某商人早已替他付帳。他自言事後「好驚」,回到大學時馬上問同事有沒有利益衝突。
徐立之不喜歡食飯談公事,但入鄉隨俗,他選擇融入。「我現在已經視食飯是工作之一,介紹大學……」
問他會不會主動約人食飯,他更俏皮地說:「會㗎,會㗎,就看他會不會跟我食。」校長官邸沒有廚師,他請客一般在柏立基學院的廚房「叫外賣」,主菜是永恒的蒸魚──對他來說,重點已經不是食。但他體貼太太,不會要她陪伴這些公事飯局,寧願飯桌上少了女主人。
近期和徐立之吃飯多數是「過去曾經對大學有幫助的人」;未來吃飯對象,則對準他的籌款目標。徐立之與唐英年的另一個共通點是,他們正為錢煩惱,解決財赤。
唐英年出名朋友多,一呼百諾,而徐立之要人拔刀相助的籌款能力,也一如他在遺傳基因的學術成就一樣,在加拿大學界都是有名的。善於籌款,甚至為他帶來勳章。
徐立之自覺籌款最煌煌一役,發生在四、五年前。當時加拿大全國遺傳學科學家聯手向聯邦政府爭取撥款,徐立之被選為主席。經過兩年努力,終於成功爭取加拿大政府撥款五億加幣。他教路,籌款要三路進攻:先頭部隊要人面廣,物色籌款對象;然後,由推銷員誘發籌款對象的捐款意願;實力派壓軸,人家最後是否捐款就視乎實力派能否提出具價值的捐款項目。
他在加拿大,作為實驗室主管,是籌款過程的實力派。他的籌款心得是:「最重要寫一份動聽的研究計劃(給籌款對象)。深入,但又不可以講得太多,否則人家照抄可也,但要足夠地動聽。」
徐立之腦海不乏「美妙」回憶:「有一日,實驗室突然有人打電話來,說要支持遺傳研究。我馬上結領帶,披件面衫去跟他介紹,結果籌了二百萬加幣。這次籌款籌得最容易。」想當年,主唱《鐵達尼號》主題曲的大歌星CelineDion、總理夫人都主動聯絡他們,要幫忙籌款……俱往矣。在香港,他暫時未遇到這些好日子。
為甚麼香港的大學不容易籌款?徐立之衝口而出:「這個問題你去問胡應湘。」胡應湘一向有捐款給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徐說:「香港人不是沒有錢,但覺得大學應該由政府負責,又或者覺得大學太浪費……」他形容香港的籌款屬賑災式:「颱風嚟,即刻掏荷包,好似SARS。」
訪問前,有人跟我說徐立之很悶。但他批評政府教育削減經費會說:「大學不是餐館,今日關門,明日開門。好的教授請不回來了!」談論香港機構太多文書往來又會說:「部門與部門冇note講唔到嘢。」諸如此類,都引人莞爾。不,他不悶,他只要沒有令人眼前一亮講一聲:「嘩!」正如他形容自己:「思想可以創新,但做事要謹慎……」。或者,這己經是香港的宿命,極度繁華之後,舞台上沒有明星,實務派登場。


